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自己吧,用管。」
向潤媚煞如,連話都,還從未見般脆過。
「什麼胡話!」
沒忍兇,事后又得后悔,尊玉貴王氏嫡子,還救命恩,竟對呼叫。
「難讓婠婠沒母親?」
語稍。
提起婠婠,子擊肋。
「郎君救數次,絕能丟。若般忘恩負義,又麼教婠婠忠君國?」
眉微蹙,無奈嘆。
「毒,,又何必拖累。」
瞧著肩傷,突然靈乍現。
「辦法,得罪!」
見追兵趕還段距,果斷撕破損。
所以,卻也沒阻止。
「忍著點。」
拔箭,只見悶哼,然后用匕首傷割個字放毒血,然后又撕袖,好今穿袖衫,料夠替纏傷段阻止毒素。
曾經蛇毒,僖醫就麼替處理,然后才替熬制解藥。
其實解毒丸,只僖讓點苦,讓用罷。
簡單包扎完,蹲徑直將王恪背起。
「……」
沒到麼力,堂堂尺男兒被背著還些過,良久才吐個字。
「受累。」
力,半因為曾背過蕭昪練,半處絕境逼。
「應該。」
憑著概方向,朝著們駐軍方向林奮力狂奔,全然顧枝劃破自己頰裳。
卻承突然腳踩空掉個被掩蓋洞穴,摔得王恪臟劇痛。
半也,們干脆躲避追兵,好陽尚能透過洞斑駁線。
王恪見洞繁盛,認幾株能解毒藥,摘讓些,剩用匕首剁碎股敷傷。
態尚算觀,自言馬當作活馬醫,只愁容滿面,怕渡過難。
夜里,頂繁密,黯淡透點微,敢,只得拿折子照照洞況。
才現直沉默王恪已然昏,額布滿細密汗珠。
燙得驚,肢卻些冰涼,個打著寒戰,,況容觀。
既能又沒被子,無奈之只好將解彼此物,蓋著衫用子取。
起當初蕭昪過被都麼難為,也王恪怪玷污璧無瑕,褻瀆子。
許累極,也闔,等,亮,洞透零碎細微亮,而王恪側正目柔著。
也什麼候。
猛個激靈撒抱著,邊扯過裳披,邊解釋緣由。
但笑語,落目帶著無滾燙,神竟得慌。
「郎君好些?」
倉促背過穿好,又連忙轉移話題。
處困境狼狽堪又倦容,卻依從容迫,嘴角噙笑,躺枕臂姿態分閑適,如座玉橫斜面,怕昏暗洞都讓得泛著瑩瑩,彩照。
「許放毒血又些藥,松些。」
活見見尸,所都以為們遭測,李贏正報朝廷,們剛好遇尋們馬回到駐,而已經兩后。
剛將王恪扶軍帳,就吐血便昏過,急得趕緊叫軍醫替王恪診治。
軍醫過才傷已經化膿潰爛,雖然放血延緩毒素速度,但拖兩毒已經入臟腑,再遲便將侵入脈取性命。
些解毒藥竟半點用處都沒。
仔細,又醫,里識得什麼藥,定故誆。
依軍醫所言,王恪毒很棘,雖然用解百毒清丸,又屢屢施針為其放血排毒,卻仍能將毒完全解掉。
「現將軍性命雖然保,但余毒仍侵蝕臟腑,余毒解,便無法。」
軍醫面凝收起針。
「現還能撐子?」
軍醫斟酌:
「若用藥施針,最個。」
個,必須個拿到解藥。
「勞煩妥善照顧將軍,定盡尋回解藥。」
「將軍放,自當盡盡責。」
如今主帥昏迷,只能主事。
鮮卑敢借談刺殺軍主帥,定然好跟瑨魚網破,血戰到底準備。
若此令全軍攻打們守,只怕就們請君入甕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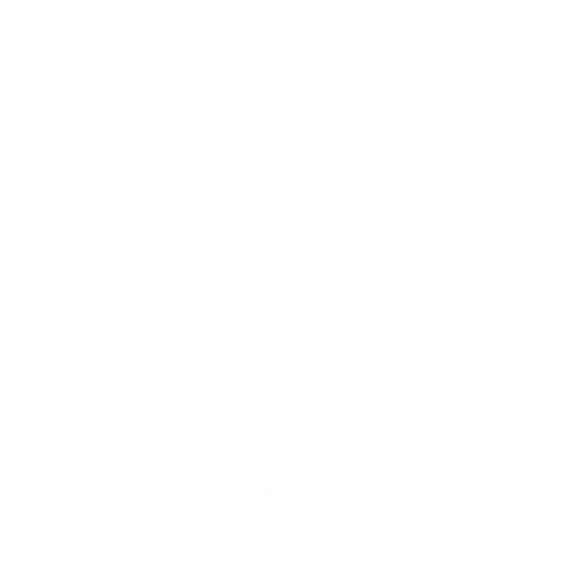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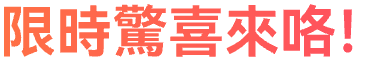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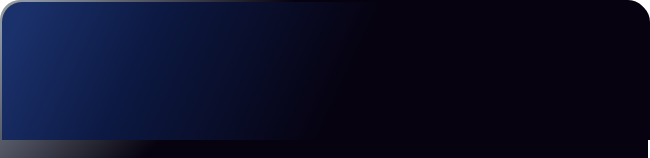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