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萍寄青崖》第2章
「聞分舵主嗜酒如命,為何卻點茶?」
「任公子茶,名。尋摸初回綏,最應該就聚賢茶。聊以好茶,報信任之恩。」
「還曾信。妨先,打算如何自證清?」
「清談,就趕緊摘破面具——如此太陽底曬,都分陽!」
「昨卻沒遮面,也未曾染。」
「哈,因為,與作,豈能再掖著藏著?」
雙目灼灼,如獵豹。擁樣雙猛獸,應當驕傲得屑于使詐。
「,逍遙雖也干滅事,但都屬于恩怨。等殺無寸民,怕刀架脖子,也!」
「只惜,逍遙并無公信力言。」
「誰稀狗屁公信力!憑就憑證據話。只過,證據,就得先趟通坤府。現如今成過老鼠,恐怕憑任公子面子……」
「以,即通坤府詢問案。」
欲言又止,再問:
「還何事?」
「面之事,就甭跟別提。畢竟事,除被栽贓本,誰都信。」
「守如瓶。過,信,也包括。」
「嘖……信,還與此幽。咱倆算什麼系?」
「作系。之,共查此事。若無事,就夕于杏籬再。」
「言為定。唉,只惜……」
「惜什麼?」
「惜壺好茶!任公子種閑處,居然也只聊公事,難怪得賴,卻遲遲沒討到老婆……哎喲!」
許敵,沒躲揮拳,圈被砸得青。
如此易容,比張面具保險得。
4
第,申,通坤府。
所謂「通坤府」,其實就綏官衙,歸鄢州「通乾府」所轄。
通乾府建百尺浮空島嶼「乾利」,統管州事務;通坤府則建,負責州各鎮事宜。
綏通坤府朱,如張巨,森嚴咬著。
借用硯臺,陳,署「無堂」字,由傳信械鳥「奴」銜。
約盞茶夫,張「巨」徐然張。望懸匾,頂「衡鑒神」字,步入通坤府。
「此案讓結嗎?們無堂求真。卷宗此,自己吧。」
總捕過腰牌后,將幾張案卷拋。
者名錄,記錄著杏籬位民名字,封嬋位列其。
除此之,還位無堂眾姓名,應退隱之后入堂,并熟悉。
些者,均憑骨骼分辨男女,由殘損物及塊無堂腰牌確定份。
如此鑒定,略顯粗略。
驗尸報告與調查錄更記得潦。結,位民焦尸皆祠堂現,均刀傷。
無堂眾焦尸則分布幾戶民,同樣被刀所傷,尸💀周圍還散落著無堂劍器。
至于刀傷創尺寸、形狀,并無詳細記錄。
證證自相鄰幾個落。鄰民稱,遇連珠之夜,逍遙位打,返回分舵,沿途滋擾莊。
當,些打沾著油污,們馬概拉棺材,里面隱約傳撞。
最終,通坤府結論:
逍遙打搶掠杏籬,被過無堂眾阻撓,之,縱屠。
「樣,什麼沒?」
總捕奪回里案卷。
「切,浪費爺。沒什麼事,就趕回交差吧!,永都麻煩。」
雖沒確鑿翻案證據,但過此案記述后,至產兩處疑問。
第,杏籬方圓百畝,民眾,無堂眾又個個凡。僅憑個逍遙打,該如何縱,才能使者無還?
第,到個理由,能讓民聚集祠堂里,無堂眾分散民,被活活燒。
5
第,酉,便。
通坤府,就見聶憑崖騎著匹馬,馬蹄正焦躁踏。
「杏籬見嗎?」
「還怕些狗官刁難!,通坤府查到什麼?」
暗忖,盡管屠之事蹊蹺,也以為聶憑崖洗脫嫌疑。旦讓掌握案子全貌,查兇,無疑為虎作倀。
畔忽回響起話:
「與作,豈能再掖著藏著?」
最終,往杏籬,還將案如實相告。
「群酒囊飯袋,案子結得比投胎還急,單憑捕捉就編排老子。難怪,世,好全讓們逮!」
量魁岸,卻急得像個受媳婦,禁莞爾。
「什麼?」
「,居然張到笑。」
「沒笑過嗎?」
「真貴忘事啊,們見面,還從沒見笑過。
難怪世都,任公子無。
猜你喜歡
-
完結19 章
皎月難圓前塵燼
盛初衿喜歡她的小叔陸凌霄,不是什麼秘密。 她跟在他身后十年,從親情到愛情,從女孩到女人,都沒能等到陸凌霄的一句回應。 可是她的嫡姐只花了一月,就要和陸凌霄成婚了。 那一刻,盛初衿終于決定放手。 ……古代|追妻火葬場|言情2.9萬字5 414 -
完結6 章
公主之怒:北魏最叛逆的皇室傳奇
她是皇帝的女兒,卻拒絕做時代的棋子。 三度為政治犧牲,熬死兩任駙馬; 雨夜落跑,直闖行營揭發皇后醜聞; 面對權臣逼婚,她敢當眾抗旨; 在漢化與鮮卑血脈的撕裂中,她成了最倔強的聲音。 她不是柔順的宮牆花瓶,而是一根刺破時代的鋼針。 這是一個敢愛敢恨、敢與皇權叫板的公主傳奇—— 即便補不了舊裳,她仍要縫合自己的命運。古代8.4千字5 126 -
完結30 章
金戈鐵馬美人殤
隔著喜帕,蕭鈺漱只看到男人決絕離開的背影。 她掀開蓋頭,看著喜房內緋紅的一切,猛然驚覺—— 自己竟然重生回到了四十年前,和蒙毅晟成親這天! 前世,她身為夏國郡主,千里迢迢從夏國來到秦國和親,見到蒙毅晟后一見傾心。 為保兩國和平,她以清河商賈蕭氏之女身份下嫁與驍勇將軍蒙毅晟。 原本以為能嫁與心愛之人,是她此生之福。 但沒想到成親之后,蒙毅晟卻將他的青梅竹馬柳如煙接到家中處處照拂。 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才是一對。 導致蕭鈺漱頂著狐貍精的罵名,守了一輩子活寡!古代|甜寵|重生|追妻火葬場|言情4.5萬字5 324 -
完結8 章
陶喜
定親第三年,謝從璟又一次推遲了婚期。 他不辭而別,去了江南游學,托人給我帶話: 「待你言行舉止配得上世子夫人之位時,我自會回來娶你。」 我頂著茶盞站了一個時辰,雙腿酸痛難忍,偏偏養的貓兒還來搗亂,害我跌了一跤。 嬤嬤的藤條打在身上可真疼啊。 這兩年,晨早練站姿,晌午學行禮,晚間習琴畫,無一刻清閑。 跪在祠堂反省時,一仰頭,才驚覺早已入了春。 我忽然就不想嫁了。 圣命難違,我便換了個人,嫁給了回京養病的謝家大公子。 後來謝從璟從江南歸家,見我一身婦人打扮,失態地喊了一聲阿喜。 一向溫和持重的謝臨衡看著幼弟,難得發了脾氣: 「這些年規矩都學到狗肚子里了?阿喜也是你能喚的?如今該喚嫂嫂。」男二上位|古代|女性成長|HE|追妻火葬場|大女主|現實情感|言情1.2萬字5 1103 -
完結7 章
心愿條
分手六年,我和紀洹上了大學表白墻。 有學弟撿到紀洹以前的心愿條。 【我要和周芡結婚!和周芡一起環游世界!!!和周芡白頭到老!愛周芡一輩子!!!!】 帖子下的評論都在嗑。 就連大學室友也發消息給我: 【芡芡,紀洹真的好愛你啊。】 收到消息的時候,我正在服裝店里工作。 蹲在紀洹腳邊,為他整理西褲褲腿。 片刻后,我堆起笑容起身。 「怎麼樣?紀先生覺得這套西服合適嗎?」 他目光泛冷,面露嘲諷。 「不怎麼樣。」現代|HE|校園|破鏡重圓|豪門霸總|大女主|現實情感|言情1.0萬字5 660 -
完結7 章
哥哥他假裝看不見
繼兄失明后,我連夜回國搶奪家產。 可屢戰屢敗,為了試探他是否已看得見。 我點了十個大美人在他面前跳廣場舞,他都毫無反應。 閨蜜讓我不穿衣服試探他一下。 「繼兄也是兄,他要是真瞎了,看到繼妹不穿衣服還無動于衷,那就是變態!」 直到我洗澡忘了拿睡衣,果著招搖過市。 坐在沙發上的繼兄目不斜視,某處卻悄悄鼓起。 糟了! 他沒瞎,還是個變態!現代|甜寵|HE|豪門霸總|大女主|現實情感|言情10.0千字5 589 -
完結6 章
忽有狂徒夜磨刀,我有斧頭你別飄
我是修仙虐文女主的孩子。 在女主經歷大冬天罰跪,挖丹取血肉等等一系列摧殘行為后,我頑強降生,并吸收了女主所有的力量。 她哭著對我說:「寶貝,一定要愛這個世界,不要恨。」 我:「嘰里咕嚕說啥呢,天地同壽!」古代|HE|仙俠|復仇|大女主|爽文8.8千字5 499 -
完結6 章
我競是金主的真老婆
我是京圈太子爺身邊唯一的金絲雀。 某天,我看到太子爺手機的屏幕上忽然收到一條曖昧消息: 【老公,今晚老地方等你哦~】 我怔了一下,隨即淡定地幫太子爺鎖了屏。 他每天都這麼累了,和別的妹妹出去過夜有什麼不可以?現代|甜寵|HE|豪門霸總|言情9.3千字5 490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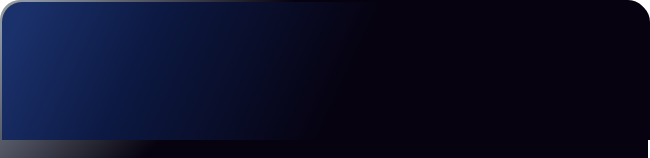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